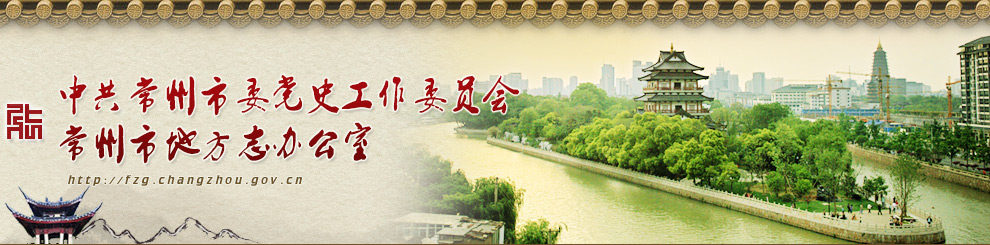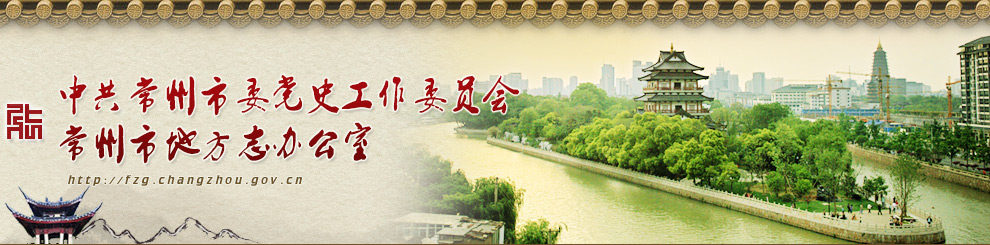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起义爆发,由此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说到武昌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而说到湖北新军不可不论及协助张之洞创办湖北新军的吴殿英。
吴殿英,字佑孙,1842年生于常州,光绪年间举人。自1888年起在浙江平湖任县令,人称“平湖公”,有“亲民、厚民、办学、育人”的口碑,甚孚众望。1895年,吴殿英卸任,由常州同乡、张之洞首席幕僚赵凤昌引荐,拜谒了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知悉吴殿英在平湖的良好官声,赏识他拟办南瀛书院的计划,相互间又有“练兵求强”的共识,因而诚邀吴殿英留幕府备用。
组训精锐之师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朝野兴起“整军经武”、“改革军制”的呼声。1895年,恭亲王、庆亲王等采纳德国军官冯•汉纳根的建议,在天津组建定武军,后袁世凯接任,更名为新建陆军。同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德国军官负责训练。1896年,张之洞返湖广总督本任,临行前从自强军挑500人,组建湖北护军,即湖北新军前身。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同意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训新军军官。一时间,湖北与直隶成为各省新军建设的榜样。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赴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赴湖北受训。因此,湖北的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其影响远逾一省,实达全国。
1896年,张之洞委任文官出身的吴殿英为都司衔监操官,担负组训新军的要任。吴则不负重望,在组建湖北护军,进而组建湖北新军方面献谋尽力,创榛辟莽,卓有建树。
1898年,张之洞委派首批五人赴日本考察军事,有直隶州知州姚锡光,游击张彪,都司衔守备吴殿英,五品顶戴千总黎元洪,东文翻译生瞿世英。在这五位中,姚锡光从日本考察归国后即调安徽任职,张彪、黎元洪返鄂后任湖北新军军官,瞿世英是翻译,他们回国后都没涉及湖北新军及湖北武备学堂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吴殿英文官出身,有较高学术素养,有办学资历,是此次“游历详考”日本军制及各种学堂章程的重要整理者。部队的编制及组训方法,武备学堂及其他军事学堂的办学规则、课程设置、授课之法,吴殿英“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一切都“务详勿略”。
回国后,吴殿英制订了湖北新军的组建规程、训练方法,湖北军事教育的高等(武备学堂、将弁学堂)、中等(武普通中学堂)、初等(陆军小学堂)三级教育体制。他还主持撰写了《湖北新军练兵要义》,其主要内容有:一,入营之士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二,人人皆习体操;三,各营人人操炮;四,马队不设马夫;五,营房力求整洁,宜于卫生;六,器械资装随身具备;七,待兵以礼;八,统带、营哨官皆亲身教练,不准用教习;九,将领、营官、哨官不许穿长衣;十,阅操之时,各官皆不许坐看。
在吴殿英等人精心操练下,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一南一北、一中央一地方最精锐的两支新式军队之一。1906年,南北两军在河南彰德举行大会操。北军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的第三镇,南军则是张之洞训练的第八镇。南军行前,张之洞在吴殿英陪同下到演兵场检阅壮行,各国驻汉口领事也应邀参观。湖北新军身躯强壮,军容整齐,枪械精良,马步、枪、炮各兵种技艺娴熟,攻防战术运用得当。不仅令中国官员耳目一新,也使外国领事惊叹。这次南北会操的结果是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平分秋色,湖北新军由此声名大著。
容留革命志士
吴殿英组训的湖北新军从装备、征募、训练到管理,都有别于旧式军队。较之中国旧式武装(如清代的八旗、绿营及练勇),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废止戈矛土铳,代之以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第二,编制、训练仿效德、日;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募兵对象为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第四,指挥官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第五,对入伍者的年龄、体格、文化程度都有规定,尤其是要“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保证了新军官兵的较高文化水平。湖北新军组建之际,适逢“废科举”,大批读书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转而投笔从戎。大批青年学子入伍,更便于部队掌握新式武器、接受近代化军事训练,也为革命党的宣传及组织活动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同为新军,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六镇是清廷的中央军,统帅袁世凯及手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是军阀型人物,对军中一切“异端”活动严加打击,因而北洋军极少有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故北洋军在清末民初一直是一支反动武装。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相对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人物虽然也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大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新军中发现党人活动,往往作调离处理了事。加之张之洞有“惜才”之好,对于某些有革命倾向的干才暗加保护,如当有人告发吴禄贞为革命党,张之洞只将吴调离湖北,而且推荐到朝廷,赴北京练兵处任要职。吴殿英也是思想开明,支持革命党,爱才用才,对新军中下级官佐爱护有加。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纯朴农民聚集一堂,又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至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共15000人,直接加入共进会与文学社等革命组织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有4000多人,站在清廷一边的不足千人,其余一半人处在中间状态。辛亥武昌首义由这样一支新式正规军队而发动也就决非偶然了。
张之洞1907年调北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先由陈夔龙继任湖广总督,后由瑞贗接任。瑞贗就职后询问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答曰:“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这一估量大体不错。
1907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政治嗅觉敏锐的慈禧洞见到湖北新军中蕴蓄着主事者主观愿望之外的历史能量。这种能量在1911年10月,即慈禧身后三年、张之洞身后两年便得到了充分展现。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欧阳萼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张之洞大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与此恰成反照,孙中山1912年4月访问首义之区武昌,详考张之洞在此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为首义爆发奠定基础,深有感慨地说:“张文襄乃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无论是革命家的盛赞,还是保皇派的挽歌,都从不同的侧面肯定了张之洞率领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巨大历史功绩。
吴殿英为创办和训练新军,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心力交瘁,更因诸多事情有违朝廷意旨而饱受排挤打压。加上张之洞后来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新军中的革命党也受到整肃,吴殿英逐渐失势,心境更加恶劣,肝郁不舒,还患上肠胃病,久治不愈,于1907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