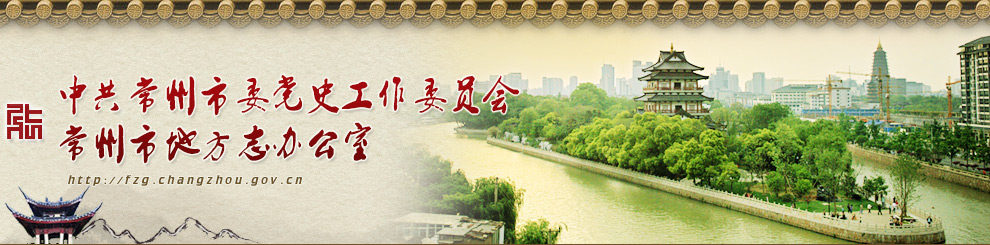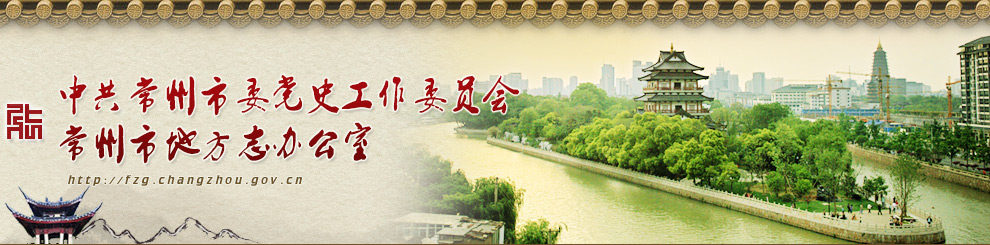熊翀,字腾霄,号正庵,河南光州(现河南潢川县)人,明成化七年(1471)七月至十一年六月任武进县知县。
熊翀是成化五年进士,不久便任职武进。在武进时,他颇有政绩,《武进阳湖合志·名宦传》称其“有经济才,立均田法,抑兼并。又因田定赋,吏不得为奸。尤加意学校,建东西楼,尊经阁、射圃、馔堂,凡陶甓木石,悉令可久。及去,士民立碑县门”。他在常还曾疏浚河道(见清庄存与《浚河记》),建惠民桥。成化十一年(1475)熊翀升任监察御使;后任山西按察副使,右佥都御使巡抚山东,右副都御使巡抚陕西,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等。他在弘治六年(1493)任职山西时,曾重刻过他的光州前辈、元代文学家、诗人马祖常的《石田先生文集》,在山东任职时(弘治十二年),曾鼎新过德州“董子书院”(汉董仲儒的读书处),说明他对文化教育是颇为重视的。但是,随着官越做越大,恐怕他保官、邀宠心理愈发强烈了,有些事就给人留下了话柄。
当初,河北蓟州民田多为牧马草场所侵,贫民失业,矛盾纠纷很突出,弘治皇帝就派当侍郎的熊翀等人去勘察调查此事,但查来查去都弄不清地籍关系。弘治皇帝不满意 ,又派了一个叫张泰的官员前去查,结果张泰求得了永乐年间的地籍,结合其它资料参互稽查,证实“田当归民者九百三十余顷”(见《明史·列传第七十四》)。为什么熊翀竟查不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没有尽力。或许他有不肯得罪权要等难言之隐吧!
更为可笑的是,弘治十三年(1500),时任陕西巡抚的熊翀奏报皇帝说,鄠县农民毛志学开河时挖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宽一尺四寸,厚二寸,上书“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的字样,现进献给皇帝。
传国玉玺是秦灭六国之后,赢政以和氏壁(一说是用蓝田玉)雕琢象征皇权的印信,上书篆文八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自此,这方玉玺就成了君权神授的符命,并随着朝代的更迭,屡易人手。拥有传国玉玺的皇帝,以此自视为正统,而没有传国玉玺的皇帝,则被视为“白板天子”,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南齐书·舆服志》曰:“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自五代时期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自焚身死,传国玉玺就开始下落不明。虽然此后的历代皇帝都竭力淡化传国玉玺的影响,并不断刻印新的玉玺,但作为君权神授象征的传国玉玺一直是皇帝们十分想要得到的东西。故从宋至清,历代都有自称发现了传国玉玺,并进献皇帝的闹剧发生,但其实这些玉玺都是伪造的。例如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咸阳有个叫段义的农民翻修房屋,挖地掘得一方玉玺,进献朝廷后,经过以蔡京为首的十三名朝臣鉴定,认为就是秦皇赢政所制的玉玺。虽然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多,《宋史》曰:“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但无奈蔡京一众权臣势大,其它人反驳也无效。实际上,这是蔡京等人策划的一个欺骗宋哲宗的把戏而已。这方伪造的玉玺,后来随宋徽宗一同被金人掳去,不知所终。再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使台都事阔阔术向朝廷报告,名将木华黎的孙子拾得家中有一方玉玺,御使杨桓受命前往辨认玉玺的篆文,确认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遂据此认为是传国秦玺。由于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刚刚驾崩,主持大事的皇后便赐给进玺的拾得钱钞二千五百贯,阔阔术也获赐两块金织文段。元成宗铁木耳嗣位后,认为阔阔术在此事中有功,便提升他为汉中廉访佥事。不过,经明人考据,元代的这方玉玺,上刻螭形,而非传说中的“五龙交纽”,也没有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时在玉玺旁加刻的“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肯定是伪物无疑。
熊翀作为文化人和朝廷大臣,对这些情况理应知晓,应该知道眼前的玉玺也是个假货,但他还是要进献给皇帝。结果礼部尚书傅瀚说:“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失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篆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弘治皇帝认为说得对,于是将这方玺收藏在宫里,避免让伪物流传在民间。对挖到玉玺的毛志学,仅给银子五两,薄赏了事。而对献玺的熊翀,没有任何赏赐。笔者想,玉玺虽然是假的,但毕竟是玉石做的,当破烂卖恐怕也不止五两银子吧?由此可见皇帝对此事的态度。熊翀等献玺,本想邀功讨赏,不料虽未被谴责,也讨了个没趣。
(见《明史·傅瀚传》,《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万历野获编卷一·卷二》等) |